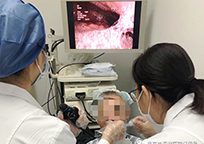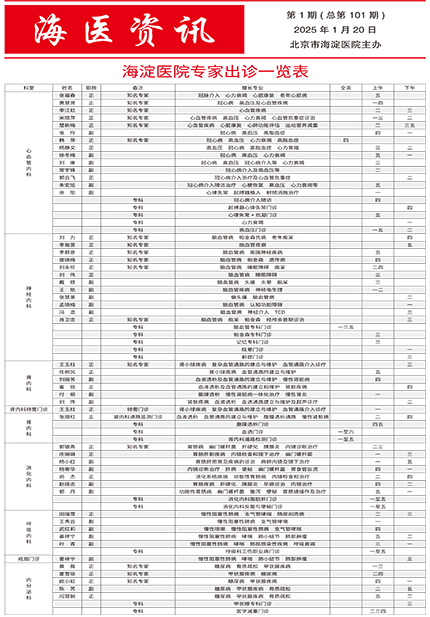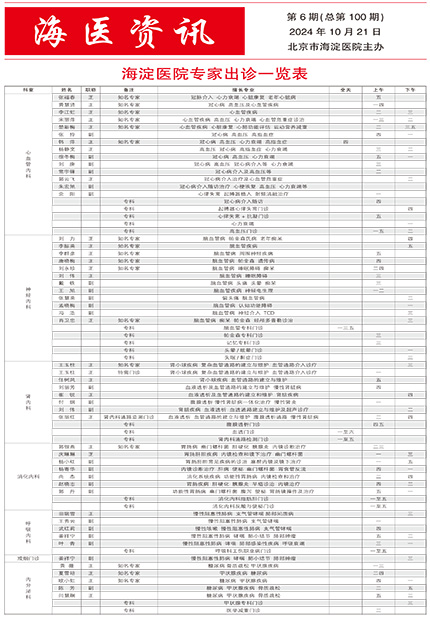往事追思 高干病房 刘岱兰
我这辈子工作单位只有一个——海淀医院。从住院医师到主任医师,当了三十三年医生。目睹了海淀医院的巨大变化。现在的门诊大楼、住院大楼高高大大,里面宽敞明亮,现代化医疗设备应有尽有,中央空调供风供暖,四季常温。
一九七零年八月我来院时,门诊、病房、药房全在临街的工字型二层小楼里,床位一百多张;后面一座三层小楼,一层是食堂,二层是男宿舍,三层是女宿舍(此楼还在),一排平房是院部办公室,全院职工二百多一点。远处看海淀医院不算矮小,因它四周不是平房就是空地。
当时文革中期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,造反派掌权,卫生员一度当医院革委会主任。医院的岗位来了个大调个,实行护士当医生,医生当卫生员,个别卫生员当上科室领导。盛行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,医院里资深业务骨干,有些被下放到郊区农村,支农,客观上也算好事,他们为农村卫生院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,只不过,多一件事——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有些留在院里当卫生员,内科王修鼎主任就正在当卫生员,我在他的带领下打扫卫生、给住院病人开饭。在不能坐诊的情况下,我只能偷空儿溜到急诊室,看抢救病人。
一个危重病人被抬进急诊室,几个医生护士七手八脚地忙起来了。然而,病人越来越重,呼吸困难,神智不清,这时来了一位中年妇女,中等个儿,不胖不瘦,带一副眼镜,步伐轻快,脚下都带着风。接过白大褂,刷刷地穿上,带上听诊器,边检查病人边指导用药,瞩咐护士密切观察血压、呼吸等。医瞩简短而清淅。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密切配合。大约二十多分钟,病人神志逐渐恢复,喘憋缓解……我想,这人是谁呀!疑惑间有人告诉我,她叫宣清华,本院的内科大夫。刚从郊区医疗队回院开会被叫来参与指导抢救。初见宣清华,她让我佩服。在医院这些年,宣清华大夫对我的影响最大,她实际上是我的导师。她医术高,抓业务。当内科主任和后来当副院长,从来不愿意坐办公室,而是下到第一线,坐诊室,查病房。我们年轻大夫也都希望她下来,真能学到本事。她家住城里,可能是离医院最远的,可是她天天提前半小时,甚至一个小时到医院。她的办法是坐头班车。有主任示范在先,谁还好意思迟到。一年半夜下了瓢泼大雨,早上骑自行车上班,门前马路积水最深处没车轱辘,摊上的西瓜漂得满街都是。我只好返回家,撂下自行车,趟着水去上班。结果迟到五分钟,诊室已经整理得清清爽爽,只有宣主任一个人,她很严肃地对我说:“怎么才来,知道下雨,应该提前点离家”。说完她就继续看病人。我心里这个委屈,一天都不高兴。下班时,宣主任叫住我说:“我刚知道你今天应该休息,还冒雨来上班,我错怪你了,犯官僚主义,向你道歉”。我一听,立刻心里热乎乎地。这是宣主任唯一一次批评我,结局是道歉,感动得我说不出话来。
当年医院编制一度实行军事化,内科、中医科、诊灸科每科叫排,加在一起算一个连,一位中医大夫当连长。正赶上“中西医结合”被作为革命口号提得最响的时候,有人提出用罗卜缨子搓心前区,治疗心肌梗塞。我疑惑,嘴快:“这样做病人受得了吗?会搓死人的”!捅娄子了。遭到连里上纲上线地批评,是政治态度问题。还好,没点我的名子。可能我一个小字辈的,不值当。私下里,年长些的大夫们,没少提醒我,少说话,说也不要太冲。不久,军宣队进驻,队长姓万,是解放军三零七医院大夫。立即在全院大会上宣布:医生、护士、卫生员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,该干啥干啥。回应的是长时间地鼓掌。
文革中,最腻歪人的是下班后连轴转政治学习、批判会、讨论会。天天搞,有时开到八、九点。我们年轻医生护士们有吃奶的孩子在家,屁股下坐的哪是椅子,是针毡,心里火急火燎地盼着早点散会。有一次九点多钟才散,天下着大雨,外面一片漆黑。我急了,当着散会人群,哭着骂起来:“天天开这些破会,倒粪似地罗索个没完没了,还让不让人回家”!王修鼎主任过来象哄小孩似地:“别说了,别哭,我送你回家”。当时我住在三义庙,租农民一间九平米低矮小房,房侧路边上有个大粪坑。一路上没有路灯,土路泥滑,坑坑洼洼的,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半个多钟头才摸到家。王主任感触:“是够困难的啊”!然而,送了我,他还要冒雨走多远路才能到家!王主任老大哥式地关照,至今想来,还觉着温暖。
大概是一九七五年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时,一次政治学习传达文件。我去晚了,一进门,大家说,你来晚了,罚你接着念!我边念边评论,发感慨:‘讲的真好’!旁边的人嗤嗤地笑!念完了,我还要评论,大家齐声:“什么呀,那是供批判的文件”!我顺嘴说下去:“我觉着挺好的”!全体哈哈大笑!
当年的海淀医院,医疗设备少,各项检查都按计划分配。如每个医生,每月只能分给四到六张心电图申请单,胃液分析、胆汁引流等等都有定额。记得一位病人要求做心电图,我手中的申请单用完了,病人家属冲着我大发脾气,我只能忍着,耐着性子解释。他们了解了真情,理解了,谅解了,气也就消了。这种情况是常态,每个大夫都不止一次两次遇到,然而,为此而发生医患纠纷的却很少。在仪器设备缺乏的状况下,只能凭扎实的物理诊断基础和实际工作经验、进行诊断和治疗。
1980年代初,各科向专业化发展,医、教、研开始启动。年轻医生纷纷外出进修学习。我到北医三院先后参加骨髓形态学、神经内科学等学习班。此后,又脱产、半脱产在北医分院、海淀卫校等单位从事教学四年多。不但提高了本人的业务水平,也为医院接受教学任务打了基础。
医院鼓励医生护士写科研论文,因而,各科室的不少论文,刊登在著名医学杂志上、或在全国学术报告会上交流。一次,老院长聂树柏先生,亲自带领我们几个年轻医生参家全国学术交流会。让我代表海淀医院,在会上宣读论文。我有些紧张,老院长说:“大胆地念,我们的不比别人差”!宣读时,他特意坐在第一排,频频点头,不时地树起大姆指为我鼓劲儿。论文读完,全场响起热烈掌声。
1980年代,社会上搞福利分房或部分人长工资时,矛盾比较突出。一些心眼儿小、一时想不开的人寻短见,以喝滴滴畏自杀者居多。抢救这种病人,我们都很有经验。医护配合默契,成功率很高。有一天我在急诊室当班,正在给一个病人做检查,突然同时抬进三个喝滴滴畏的人,等我忙乎完这头儿,那边护士们已把胃洗上了,点滴也扎上了。甚至第一批阿托品和解磷定都已注射,由于抢救及时,三个病人全部脱离危险。家属和单位领导都十分感谢。记得参加这次抢救的是李淑贤和田桂玲两位老护士。
史桂昌主任家住医院内,晚上经常来关照值夜班的医生护士,并常送些好吃的。端午节送来一饭盒粽子,皮儿都拨好了,大伙抢着吃,香!老内科是个团结温暖的集体,彼此相处如兄弟姐妹。主要是年长些的有大哥哥大姐姐样。
1989年医院组建干部病房后,我任该科主任。此时,共青团开展给有卓越供献的老专家、老学者送医、送药的“青年志愿者”活动。郄禄和老先生就医在干部病房,是“青年志愿者”的服务对象,我成为小组的医疗顾问。一九九四年胡锦涛同志作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,春节期间慰问走访郄禄和先生。在郄老先生家里,胡锦涛同志也亲切接见了志愿者小组全体成员。像聊家常一样,询问郄老先生的身体情况、志愿小组工作情况。口气和蔼,平易近人。志愿小组的同志们很受鼓舞。
往事如烟,往事如云,忘不了的是,一起共过事的同志们那份纯情、那种友谊。